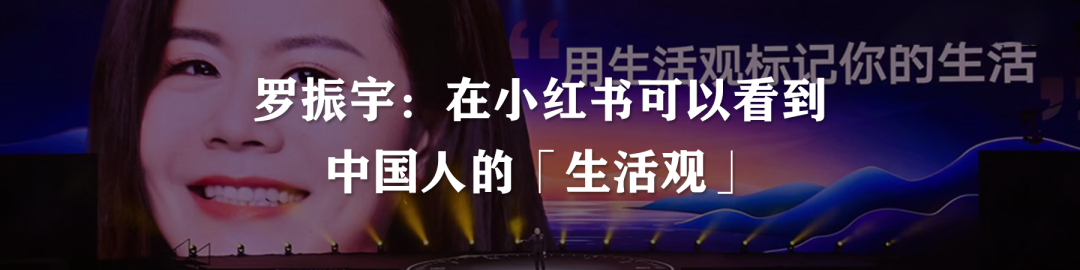黄海清当然清楚,“睡到全中国没有鬼城为止”是句空话。“寻找鬼城”的过程十分重要。他曾告诉协商员,重点不是美术馆里呈现的东西,“我们这种行走已经记录了中国的整个状态。”
作者|刘丹
“二打六”是广东话里的小人物,“鬼城”指的是资源枯竭而被废弃的城市,宽泛来看,也指入住率比较低的空城。在过去的5年里,林超文所在的“二打六”艺术小组进行着名为“睡鬼城”的行动,探访大规模的烂尾楼,像一种边缘角色对另一种的慰藉。
酷是鬼城的第一吸引力。成片荒废的别墅,修建时每栋要价上千万,现在属于流浪汉和捣蛋鬼。庞大而空旷的建筑群就像血肉剥落后的骨架,暴露出城市原始的野心和病症。二打六在这些地方喝茶、打牌、办跨年派对,蒙着眼睛寻宝。

▲二打六在鬼城放生一条金鱼

▲二打六在鬼城做晚饭
就拿广东省来说,二打六去过的就有广州市的芙蓉山庄、中山市的圣贤山庄、清远市的金福花园、河源市的儿童王国等。第一次外出找鬼城前,他们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。上路后,他们发现,鬼城完全可以偶遇。
从南到北,砖是不同的,土壤也是不同。林超文说,广东有客家围龙屋,皖南有徽派马头墙,特色多体现在传统建筑上,新建筑就大同小异了。鬼城的规模也有变化,南方建筑密集,看起来寸土寸金,越往北体量越大,“它没有其它吸引力能让年轻人过去生活。”
在成为“鬼城”之前,那些地方通常会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名字:大多是新区新城,再不济也带着“山庄”“花园”之类的气派名号。
二打六没有刻意分辨“鬼城”的概念。藏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封门村“鬼”名远扬,村庄无人居住,棺材、残碑、太师椅,灵异传说萦绕其间。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鬼城”,而是受各种自然条件限制,人口自然迁出的村子。
夜入太行,张贴门神,为封门“驱鬼”。二打六有大梦想:睡到全中国没有鬼城为止。

▲二打六在封门鬼城贴门神
更多情况下,“鬼城”空空荡荡,只在入口有保安把守。潘学城说,“那些老板肯砸那么多钱把它建起来,还差2000、3000块钱请一个保安吗?他们要看着他们的资产。”碰到保安,大概率不让进,得绕路走。
二打六不想打扰鬼城,哪怕“睡鬼城”,也是远远地睡在外面的空地上,林超文说,他们享受这种微妙的距离感,“你看着我们,我们看着你。”
仔细想来,保安才是真正睡在鬼城的人。没有同去的朋友,没有搞艺术的梦想,一个人守着一片空建筑,“这其实也很讽刺,里面根本没有人。他是很孤单,很孤独的。”
来到鄂尔多斯已经是11月。和往常不同,二打六没有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扎营过夜,“只要你走在大路上,你可以随意就能看到遍地烂尾楼的鬼城”,他们决定开车环绕城市,用三天的时间“体验中国这个最大鬼城的鬼魅”。

▲二打六在鬼城扮鬼脸
大半个中国,什么都在发生:
火山在喷,河流在枯
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
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
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
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
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
他从2011年开始跟拍小组成员,作为曾经的文艺青年和现在的打工人,祝高攀希望二打六成功。这是一种理想的投射,“他们比我努力,他们还在坚持做艺术家。”
艺术评论家胡斌把睡鬼城的二打六称为“放逐自己的集体出走”, “从艺术系统出走,也从庸常的日常生活出走。”
黄海清很喜欢这个评价。他是生活相对顺利的一位,2010年就办了画展。黄海清希望其他成员过上更稳定的生活,但也坚持要“睡鬼城”、做作品,“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”。
算起来,他们也是艺术领域的“二打六”,都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,从一所非艺术类院校出来,没有什么人脉,很少获得展览的机会。林超文、潘学城等人在2010年毕业后搬到了黄海清工作室的旁边,大家聚在伍仙桥,定期办沙龙、做展会。

▲二打六状态一
潘学城来来走走,纠结过很久。毕业后,家里帮他安排了院线经理的工作,前景很好,上班也算轻松。赶上电影《后会无期》上映,他听到主题曲《平凡之路》,决定辞职。“向前走/就这么走/就算会错过什么。”他告诉领导,想回去做自己喜欢的事,领导说,你还没玩够。
吃散伙饭那天,潘学城闷声敬酒,十几杯白酒下肚,早就断片了。同事们没发现异常,目送他精神抖擞地出了门,再看到他时,人已经醉倒在大街上。那个夜晚,未来迫近,他没有觉得解脱,而是越发紧张。
在“睡鬼城”之外,潘学城也为垃圾袋、生锈的铁钉等“被生活抛弃”的物品画像,捕捉“一千零一个梦”,“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,只不过鬼城是现实中体量最大、最明显的东西。”
几年过去,潘学城成了家,有了小孩,要画画也要养家,“一千零一个梦”只做成几十个。“反正就是去面对吧,我没有雄心壮志,但我釜底抽薪。”
在伍仙桥的日子是黄海清过去十年中最快乐的时光。2016年,伍仙桥工作室被迫搬迁,那些日子回不去了。

▲二打六状态二

▲二打六《来自鬼城的一块砖》制作现场
陈艺儿最开始觉得“睡鬼城”挺有趣。见过越来越多烂尾楼,在现实面前,近乎游戏的作品变得无力。她想起维持工作室的辛苦、一辈子背着债务的房奴,还有广州天桥下面为了驱逐流浪汉浇筑的水泥锥,“好像到处都容纳不了你。”
鬼城总是静默的,访客自己为自己提供答案。从鄂尔多斯回来,陈艺儿离开二打六,重新寻找创作方向。“当时我们没有更深入地去思考,是比较单纯、比较天真地去做这个事情。”
经过2019年的休整,黄海清打起精神,要继续往鬼城走。二打六只剩四人,他已经忘记最初大家为什么想“睡鬼城”,但那模糊的一瞬间改变了他的轨迹。“虽然这个事情看似很无聊或者毫无意义,但是我很明白,这件事但凡坚持去做,就具备着意义。”
2020年10月底,二打六在广州太古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主题展览。年轻人在来自鬼城的钢筋、鞋子、布娃娃前打卡,展览成为“拍照好去处”,“在小红书上火得一塌糊涂。”
也是在这一年,投资170亿,烂尾5年多的石家庄祥云国际作为“网红拍照胜地”登上微博热搜,宁波、汕尾等地的烂尾楼都成为“网红”。鬼城作为一种景观被欣赏,林超文觉得算是好事,“要不它们就安安静静地在那里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活。”

▲《take it!》作品制作现场
像他们登场时那样,二打六缓缓滚出盒子,回到现实里。
*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@城市OurCity原创内容 转载请联系授权
欢迎转发朋友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