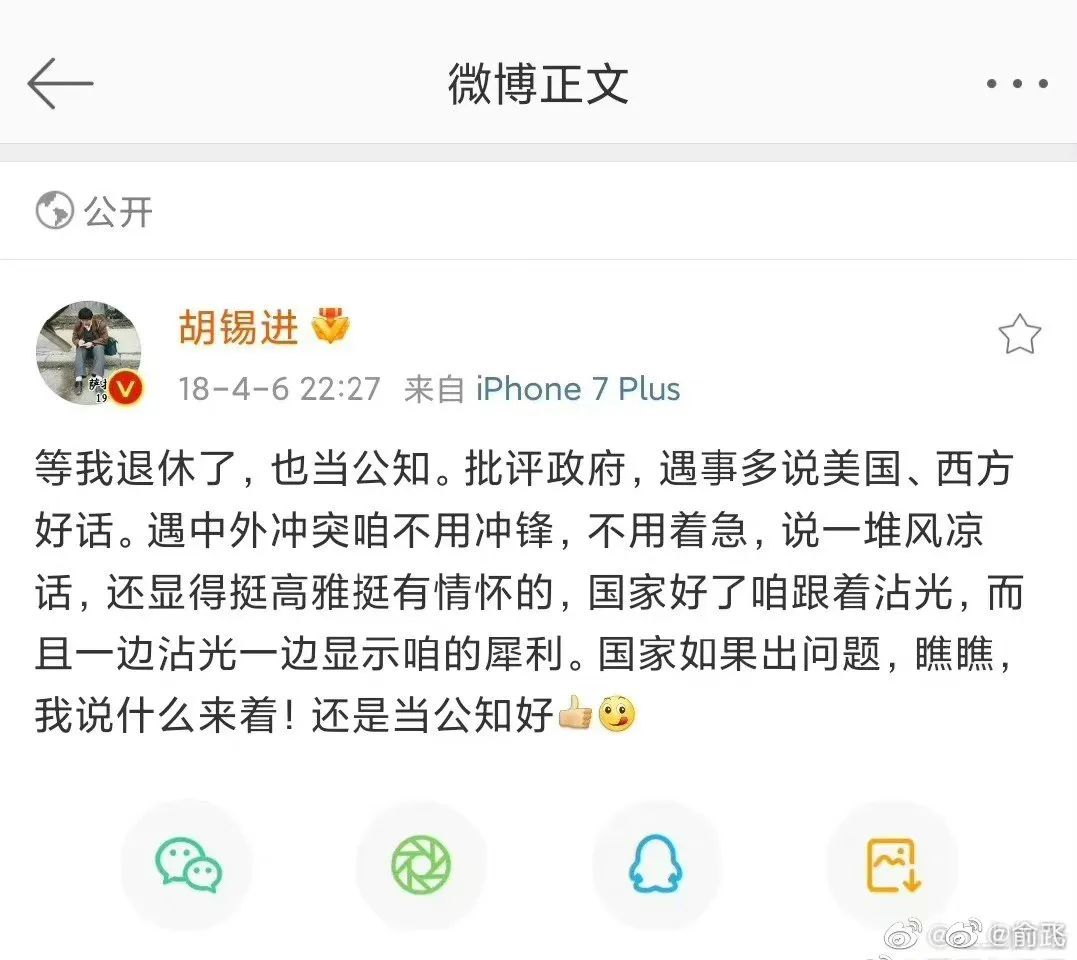二、学术标杆
狭隘、封闭的社会学界,无论生态还是心态,也夫与社会学界,不大合拍。也就是说,郑也夫能够成为这个样子,并不是社会学水土和气候作用的必然结果,甚至可以说是反方向的结果。那么,什么是滋养郑也夫的精神资源?
1977年恢复“高考制度”,也夫考取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,也许是由于用力过猛,结果反倒不大理想。按照现在的说法,也夫这班的同学都属于补录的。尽管这段时间不长,但是,也夫看待事物能够具有通达的目光,可以算得上历史系的收获。
也夫经常念叨,社会学这一学科内部的差异程度非常惊人,也许就是这一点,使得社会学在专业化建构方面,举步维艰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1979年费孝通老先生都已经69岁了,但是被胡乔木软硬兼施,硬着头皮归队。“五脏六腑”一样都没有,怎么办?只能在南开大学搞了社会学进修班,具有速成的作用。当今不少社会学的骨干和大腕儿,就是南开速成班的黄埔一期。这是1982年的事情。
当时,也夫正好从社科院世界宗教系毕业,分配到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,殊途同归,1982年,也夫正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员,带着理想,带着朝气,也带着那份属于也夫的特立独行。
历史真是妙啊!
也夫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时候,英语特别突出,齐世荣先生内心还是挺待见也夫的。无奈,也夫浑身散发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,使他忍受不了“扩招”和“补录”的耻辱,学校不给补录生提供住宿,“走读”对于运动健将也夫来说,不值一提;关键是入学的时候,由于没有单位的依托,也夫不能享受助学金,这对也夫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所以,1979年也夫用力,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研究生,每月可以获得40元补助,这在当时,可是一笔巨款。导师赵复三先生其实总共也就见了也夫十来回。学术理念各异,志趣不同,再加上老先生过度意识形态的心态,师生关系谈不上有多好。但是,导师不希望也夫走捷径,所以,也夫最初的选题被否定了。这时候,也夫的英语功底,大有用武之地,硕士论文研究的涂尔干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。从此也夫走上了社会学的道路,渐行渐远。
也夫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,费孝通先生已经领衔恢复社会学。别看费孝通既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,又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会长,早年的书生意气已经荡然无存。既然被叫来救火的,就得听从人家的指挥。心高气傲的费孝通,身边很少有看的上眼的,但是,社会学这个大筐,什么样的人物都得往里装。何建章这样的经济工作者,协助费孝通工作,费孝通是高兴呢,还是伤悲呢?没有办法,只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,其实,就是说一些场面上的话,应付一下场面。
1982年,来到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,人事档案一直到保存到1994年。1985、1986年两年时间在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社会学。“不怕贼偷,就怕贼惦记”,这是也夫常说的一句话。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,也夫就是知名的“托派”(托福考试的相关知识,比较丰富),联系出国留学,有不少法门,经常传经送宝,接受出国咨询。这时候,也夫真是万丈雄心,心潮逐浪。
也夫本来已经联系好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,但是,中国社科院比较较真和呆板,就是没有允许,也夫干着急没有办法。丹佛大学比起伊利诺斯,学术品质要差一些,但也夫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其实,80年代政治的清明和火热的改革氛围,激发了也夫的深沉思考。忙于出国的时候,似乎也顾不了那么多。但是,来到美国,沉潜在也夫内心的思考,重新充溢心中。在美国,导师不认为硕士生是什么人才,充其量只是学术的半成品而已,不读到博士毕业,导师就会很伤心的。本来也夫去丹佛大学,是奔着博士去的。只要修满足够的学分,就可以获得博士毕业。但是,也夫实在难以忍受不能写作的痛苦。导师、亲朋好友,没有人认为也夫不读下去,是一个明智的选择,好不容易出国,结果连博士学位都不想要了,何苦来哉!见到画画的堂哥,也夫整天与堂哥争辩,内心充满创作的冲动,但是整天临摹的痛苦,实在是难以倾诉的。也夫的真性情,可窥一斑!
正好也夫的学分够得上硕士,这样,也夫于1986年,心急火燎地回到朝思夜想的故国。不到两年的时间,《知识分子与中国》的书稿就顺利完成,这是1988年的4月。接着筹备召开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,会议是在北戴河开的,知识分子研究的主力,许纪霖、黄万盛、陈明、谢泳都参加了会议。据说,在会议上,这些知识分子研究者,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,达成一个共识:知识分子必须是对于专业之外的社会有所关怀的人。那时候,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,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,那时候是具有比较公认的底线认同的。1989年之后,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,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,所以,只能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定语——“公共”。因为,随着犬儒化知识分子的暴富,人文关怀和担当道义,对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,已经成为一种奢侈。
1985年费孝通老先生已经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彻底了断,来到北京大学。这对费孝通来说,也是一种寻找社区的努力。郑也夫1994年离开北京社科院,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,1998年离开中国社科院,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,2004年离开人民大学,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。这时候费孝通已经步入晚年,2005年4月24日,费孝通离开开满鲜花的田野,化作泥土。两位隔辈的社会学家,足迹有所交叉和重叠。仔细思量,确实很有趣味。
晚年的费孝通,到底做得如何?这是费孝通老先生本人的一大心病。自己仅是花瓶而已,哪里能够像张思之律师,哪怕做花瓶,也要做有刺的花瓶。1957年之后,费孝通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,已经在精神气质上被全能社会彻底打倒。晚岁回首平生,遗憾实多。情不自禁地回忆“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”。难道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,就没有费孝通的风采和神韵吗?也夫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,实在难以在当代寻找精神养料,所以,把目光投向了民国历史。在那里,他看到了一个具有智慧、悟性和才华的知识分子范型——费孝通。也夫对于1949年之前的费孝通,推崇备至。对于《乡土中国》流溢的精辟议论,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。
但是,对于晚岁的费孝通,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中所起到的作用,郑也夫并不以为然。也夫对于1980年以后的费孝通,并不看好。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成为目前病弱不堪的情形,费孝通难辞其咎。所以,2005年4月24日,费孝通先生离开人世,也夫拒绝了《南方周末》的约稿。因为,也夫,不愿意在老先生刚刚离开我们,就要进行批判,也夫觉得那样不够厚道。
但是,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邀请也夫做学术演讲,回答学友提问时,也夫还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,当然,这个想法与社会学界主流意见确实正好相反。也夫不认同社会学界同仁对晚岁的费孝通作出过高的评价。社会学界“言必称费老”的学人,坚定地把费孝通的这个大旗扛下去,晚岁费孝通小城镇调查和“离土不离乡”的构想,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有机部分,被说成是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一大贡献。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,是中国不多的具有水准的政论家和时评家,晚岁的费孝通已经彻底抛弃了40年代人权、自由、民主的理念,论证和印证了政府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政策。聪慧、世故的费孝通,明白政府的需要,这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“曲学阿世”。
也夫在深圳的学术演讲中,谈到费孝通的晚年:“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,极其遗憾。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,此前在知识界,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、非常有见识的人,一个睿智的人,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。”也夫分析,之所以如此:“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,被约束了,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,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、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。”费孝通没有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,而是将学术当作一种职业,所以,遇到环境的变化,不会把学术当作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领地,早就把学术放弃了,对待学问的实用主义态度,使得1978年以后的费孝通,只是做一些政府认为有用而且立竿见影的东西,这样可以给人证明:社会学是非常有用的,能够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。这样,在费孝通的影响之下,在政府的推动之下,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走上一条“急用现学”的路径。
大陆的社会学家,没有兴趣关心丰富生动的社会,心甘情愿做政府的助手,解释社会的能力及其有限,这与社会学共同体的不发达,互为表里,同时与费孝通对社会学的塑造,亦大有关联。
社会学家对于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,对中国社会大势的理性认知,对未来社会,所持有的理想主义,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,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。
社会学家丧失了职守,能够忠于职守的,反倒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怪物。也夫,面对晚岁的费孝通,不由自主,神往四十年代的费孝通,羽扇纶巾,英姿勃发。尽管没有达致40年代费孝通的水准,但是,也夫抛弃80年代的费孝通,这就是不简单的事情,放眼望去,多少社会学家还在紧紧抓住80年代的费孝通。
所以,对于知识界来说,有一个寻找社区的任务。但是对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而言,还有一个树立标杆的工作。不妨把郑也夫当作社会学的标杆,踏着也夫的足迹,寻找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影子。
 耍Q-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
耍Q-耍出你的范儿_分享你的福利